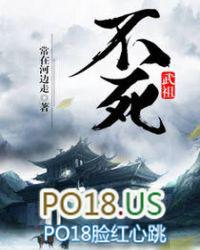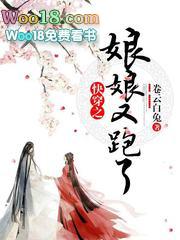笔下文学>无敌天命 > 第九百五十二章 观玄宇宙亡(第2页)
第九百五十二章 观玄宇宙亡(第2页)
苏念走出塔门时,已是三天之后。她瘦了一圈,双眼红肿,可脊背挺得笔直。她没有说话,只是回到小屋,拿起毛笔,在《问心录?终章》的空白页上写下第一行字:
>“我不是来寻求答案的。
>我只是想告诉你??我一直都在听。”
字迹落下,整本书嗡鸣震动,仿佛回应她的觉醒。书页间开始自动浮现新的内容:一位老兵在战后三十年首次拥抱了敌国幸存者;一名被拐儿童成年后找到亲生父母,却选择同时保留两个家庭的姓氏;南极科考站传来消息,冰层下的“孪生之心”旁,竟生长出一朵银白色的花,花瓣每片都映着不同语言的“回家”。
人们开始察觉,《问心录》不再仅仅是记录者,它正在成为引导者。
然而,并非所有回响都是温柔的。
某夜,西北荒漠边缘的一座废弃雷达站内,警报突然响起。监控画面显示,地下三百米处,一座被遗忘多年的旧式共感装置自行启动,连接的竟是二十年前一场失败实验的数据核心??“断忆计划”。该项目曾试图通过神经阻断技术,彻底删除人类对创伤事件的记忆,结果导致参与者集体失语、情感冻结,最终被联合国永久封禁。
而现在,那台机器不仅重启,还反向接入全球共感网络,释放出一股黑色脉冲波,所经之处,共感塔信号紊乱,银草光芒黯淡,甚至有人突然失去所有近期情感记忆,连亲人面孔都无法辨认。
消息传至南渊湖,新任守护者??原心理援助中心医师林昭,接到紧急通报。他是当年那位退役士兵阿哲的主治医生,也是少数真正理解“共感并非治愈一切”的人。他立即召集各地联络员,却发现部分成员已被黑脉影响,陷入麻木状态。
“这不是故障。”林昭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流,声音低沉,“这是报复。是那些曾被强行遗忘的人,在借机器之身创造‘反共感’。”
他带上便携式承忆炉,独自前往西北。
抵达雷达站时,风沙正烈。林昭推开锈蚀的铁门,看见中央控制室内悬浮着一团漆黑球体,表面不断浮现出扭曲的人脸:有被家暴后选择遗忘的妻子、有目睹校园枪击却被迫接受记忆清除的学生、有战争中亲手杀死同胞却被洗去罪疚感的士兵……他们的眼中没有光,只有空洞的愤怒。
“你们错了。”林昭站定,平静开口,“遗忘不是压迫,共感也不是救赎。真正的自由,是让人有权选择记或不记。”
黑球剧烈震荡,一道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:
>“可我们没得选!
>他们说‘为你好’,就把我们的痛抹掉!
>现在你们又说‘要面对’,逼我们一遍遍重温地狱!
>我们只是想安静地活着……难道不行吗?”
林昭沉默片刻,打开承忆炉,放入一段私人记忆影像??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阿哲时的场景。年轻士兵蜷缩在角落,双手抱头,反复念叨:“别死……别死……”而林昭蹲在他面前,轻声说:“你可以不想记。但如果你愿意,我可以陪你一起看。”
影像播放完毕,黑球颤动减缓。
“我不是来消除你们的恨。”林昭继续道,“我是来告诉你们:你们有权关闭门。但请别烧掉别人的钥匙。”
良久,黑球缓缓下沉,融入地面。雷达站电力中断,所有设备归于沉寂。次日清晨,沙漠中升起一道罕见的日晕,光环内隐约可见一行古语:
>“忘不可强,忆亦非缚。
>心之所向,即为归途。”
危机解除,共感网络恢复清明。而《问心录?终章》再次更新,新增一页:
>“我们曾恐惧记忆,于是发明遗忘。
>后来渴望疗愈,于是拥抱共感。
>可真正的智慧,或许在于承认??
>每个人都有权决定,自己的心该承载多少往事。”
>“而我们要做的,不是统一答案,而是守护这份选择的权利。”
这一年秋天,南渊湖迎来第十届“光语节”。千人齐聚湖畔,手持特制忆灯,将心中最难以启齿的话投入湖心。有的是道歉,有的是告白,有的是迟来的谢谢或对不起。当最后一盏灯沉入水中,湖底忽然绽放出万丈银光??那株沉睡多年的银花,终于盛开。
花瓣层层展开,每一片都映照出一个人的脸庞。它们并不说话,只是微笑,或流泪,或点头。有人认出那是自己逝去的爱人,有人看见童年失踪的玩伴,还有人惊觉其中一人竟是十年前自杀的挚友。
“它不是复活。”林昭站在高台上,对着人群说道,“它是证明??那些被爱过的灵魂,从未真正离开。”
自此,银花每年秋季开放七日,被称为“回望之期”。期间,任何人只要怀抱真诚之意步入湖中浅滩,便有可能听见心底最渴望听到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