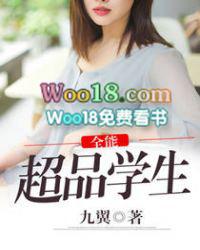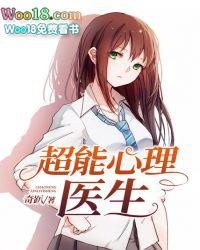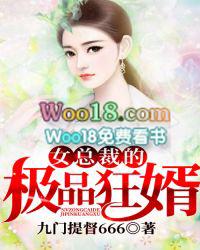笔下文学>从采珠疍户开始无限就职 > 第66章 翻手为云玩弄人心(第2页)
第66章 翻手为云玩弄人心(第2页)
第二天,她在声衡院召开紧急会议,提出“双轨制”构想:保留有限度的技术过滤机制作为安全阀,同时建立“语觉训练营”,教导人们如何与体内日益活跃的“声素细胞”共处。课程包括情绪锚定、记忆辨析、多语言自我对话管理等。首批试点设在十所中小学,孩子们被鼓励记录梦境中的陌生词汇,并绘制“内心语言地图”。
成效出乎意料地好。三个月内,接受训练的学生不仅未出现语疫症状,反而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:有人用混合方言写出预言诗,准确描述了即将发生的地震;一对双胞胎通过“梦契”共同完成了一幅描绘远古归墟文明的壁画,其细节与最新出土文物完全吻合。
然而,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春分前夕。
那一日,全球气温骤降,天空呈现出青铜色。归墟之心的搏动频率突然加快至每秒一次,所有电子设备自动播放一段未知音频??既非人类语言,也不属于任何已知动物发声系统,但却让听见的人无不流泪。语言学家分析后发现,这段声音的数学结构与人类胎儿在母体中听到的心跳、血流、呼吸高度共振,像是某种“原始母语”。
就在这一刻,世界各地同时出现了“言泉”。
沙漠裂开,涌出冒着气泡的液体,每一滴都包含一句温暖的话语;火山灰落下时,在空中凝结成发光短句,缓缓飘向地面;甚至极光也开始传递信息,北极圈内的居民抬头望去,只见绿幕之上浮现出一行行温柔的叮咛:“你还值得被爱”“你不是一个人”“说出来吧,我听着”。
苏挽站在新岛建立的“语源观测站”顶楼,望着天穹如织的光语,忽然笑了。她终于懂了林晚舟的选择。
她不是牺牲,她是播种。
语言不需要拯救,因为它本就生生不息。真正需要拯救的,是我们面对真实时的勇气。而林晚舟所做的,就是把这份勇气,炼成了基因,注入了物种的未来。
春分当日,归墟之心停止了异常跳动。
取而代之的,是一种全新的节奏??平稳、温和,宛如摇篮曲。全球“语爆”现象消失,但人类的语言能力并未衰退,反而进入稳定进化期。新生儿天生具备跨语种理解力,能听懂父母未曾教过的语言;老年人临终前常会说出几句神秘诗句,事后考证竟是失传千年的祷文。
一年后,第一艘“言舟”建成。
它不用发动机,靠收集航行途中人类交谈产生的“语能”驱动,船身由声素结晶打造,能在风浪中断续吟唱《安魂谣》变调版。首航目的地是南屿渔村,那里,石碑旁已长出一片小型言树林,每当潮水漫过碑文“我在”,整片树林便会齐声回应:“你也活着。”
苏挽作为顾问登船。出发前夜,她最后一次抚摸那本《万语录》。书脊悄然裂开,飞出一只由文字组成的蝶,绕她三圈后,落入海中,化作一道光脉,指引航路。
航行第七日,海上起雾。导航失灵,罗盘乱转。船员惊恐发现,所有人说的话都被倒放回传。就在此危急时刻,船头忽然亮起一团蓝光。一个模糊身影浮现,轮廓纤细,长发随风轻扬。
“跟着光走。”她说,声音分裂为千万重和音,却清晰无比。
是林晚舟。
不,或许不是她本人,而是她所化的意识集群中的一缕显化。但她确实存在,以语言为血肉,以记忆为骨骼,以千万人每日说出的真心话为心跳。
船员们含泪转向那道光。迷雾渐散,前方海域浮现出一座从未标注在地图上的岛屿。岛上矗立着一座巨大的贝壳雕塑,高耸入云,内部回荡着永不终止的低语合唱。
后来,这座岛被称为“终语洲”。
传说,只有真正说出过“我错了”“我爱你”“对不起”的人,才能看见它的位置。
而每当有人踏上这片土地,脚下的沙粒都会自动拼出一句话,随即沉入地底,成为支撑岛屿存在的根基之一。
许多年后,一位白发学者带着孙女来到此处。小女孩指着贝壳问道:“奶奶,这里面住着神仙吗?”
老人蹲下身,轻抚她的耳朵:“不,住着曾经愿意为别人说话的人。”
风掠过,整座岛屿轻轻震颤,仿佛在点头。
而在归墟最深处,旧神之心静静搏动。
每一次跳动,都孕育出一枚新的沉誓贝。
贝壳缓缓张开,露出内壁湿润的文字,像是刚刚写就:
>“下一个名字,会是谁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