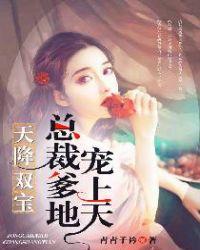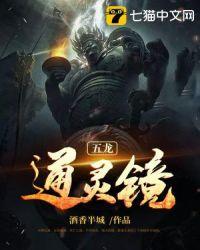笔下文学>未来,地球成了神话时代遗迹 > 第419章 摧枯拉朽(第3页)
第419章 摧枯拉朽(第3页)
信号目标明确:那片尚未命名的星域,环形碑林背后的虚空。
发送完成后,全球陷入等待。三天,四天,第七天深夜,第一道回信抵达。
不是通过语波,也不是电磁信号。
而是**全球所有镜子在同一时刻映出不同的倒影**。
有人看见自己年幼的模样,有人看见从未谋面的祖先,还有人看见未来的自己,抱着一个发光的孩子微笑。而那些曾参与“无言祭”的人们,则在镜中看到了另一个世界:那里山河倒悬,河流向上流淌,城市建在云中,居民用眼睛说话,用手势写诗。
最关键的是,每一面镜子的角落,都浮现出一行小字:
>“我们也等了很久。”
苏璃冲进控制室,却发现系统并无异常记录。“这不是外部信号入侵,”技术员满脸困惑,“更像是……镜子本来就有这个功能,只是现在才被人‘想起’如何使用。”
她忽然明白了什么,立刻联络李哲:“带孩子们来观测台,带上他们画的画、写的字、录的声音??所有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。”
当第一百二十三个孩子将手绘的“家”贴在观测玻璃上时,奇迹发生了。那幅蜡笔画中的房子突然微微发光,镜面泛起涟漪,画中烟囱冒出的烟竟缓缓飘出纸面,化作一缕真实青烟。
“物质投射!”科学家们惊呼,“信息正在转化为实体!”
更不可思议的是,其他镜子也开始响应。世界各地的家庭录像、学校黑板报、街头涂鸦墙……凡是有孩子表达过“我想让你看见”的地方,图像纷纷突破二维界限,成为可触摸的存在。
东京一位自闭症男孩画的飞船,从素描本中腾空而起,悬浮在房间中央;开罗贫民窟女孩写的诗句,变成金色文字环绕清真寺尖塔飞翔;北极科考站墙上潦草涂鸦的北极熊,踏着月光走出墙壁,轻轻蹭了蹭研究员的腿。
“他们在学习‘相信’。”塔米拉站在喜马拉雅山顶,仰望星空,“当我们终于敢相信一句话能被听见,一个梦能被实现,宇宙就会给我们看得见的答案。”
娜娜在X-9行星收到了最后一段讯息。来自语之心深处,以她童年卧室壁纸的花纹为载体,浮现一行粉红色荧光字:
>“妈妈,我把风装进瓶子里了,你要看吗?”
她再也控制不住情绪,蹲在地上痛哭起来。这是她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哭泣??不是为了悲伤,也不是为了感动,而是因为**她终于可以不用再扮演完美的教师,而只是一个想家的女孩**。
孩子们围上来,一个个抱住她。每一次拥抱,都有新的记忆复苏:地球的雨声、面包店的香气、图书馆旧书页的味道、放学路上踩水坑的快乐……
情感学校的外墙开始崩解,晶体化作春泥,草坪蔓延成森林,教室变成村落。娜娜站起身,牵着学生们的手走向远方。
“我们回家吧。”她说。
不需要飞船,不需要星桥。他们只是并肩行走,脚下的土地便自动延伸,星光铺成道路,风托起衣角。一步,两步,第三步跨出时,他们已站在地球南太平洋的海滩上。
海浪轻柔拍岸,三百二十七名孩子正等着他们。
没有言语,没有仪式。双方只是静静对视,然后同时张开双臂。
拥抱发生的瞬间,全球所有言梧树的花朵同时闭合,又再度绽放。这一次,花瓣不再是人脸,而是变成了小小的嘴巴,一张张开合,齐声低语:
>“我在。”
>“我在。”
>“我在。”
声音汇聚成洪流,冲破大气层,射向深空。沿途,星桥震荡,环形碑林鸣响,火星城市灯火通明,X-9行星的晶体森林集体发光。
而在那片未知星域,无数光点悄然亮起,如同回应晨曦的星辰。
第一声回答来自亿万光年之外,稚嫩依旧,却多了几分笑意:
>“嗯,我听见啦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