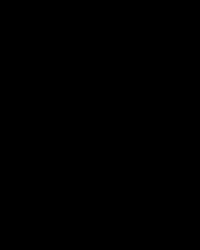笔下文学>朝露待日晞 > 濯缨(第2页)
濯缨(第2页)
陆旻眸色深沉,仍然字字诛心告诉她不容逃避的事实,“他过不去自己心里那一关,他也迟早会知道。”
宁晞眼睛酸胀,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铁了心要她直面现实的男子,压抑在心底最深处的话也如流水般脱口而出,“五岁那年,阿翁去世,我第一次体会到何为天人永隔,那时就觉得自己的心已经难受到了极点,世上应该没有什么事情会比那还要痛了,却从来没有想过命运会在八岁那年出现更大的变数,仅仅一夜之间,朝翎沦陷,整座皇宫血流成河,爹爹娘亲惨死在我面前,而我却只能用手紧紧捂住阿珏的嘴躲在暗道中眼睁睁看着,什么都不能做,什么也做不了。因为我与阿珏的生路,是全皇宫上下所有人用鲜血铺出来的。娘亲告诉我,只要活着,一切就还有希望。”
“我也告诉自己,只要我活着,我必定会让作恶者血债血偿,夏侯氏的江山,我也一定会夺回来。”
“隐忍筹谋了十年,我以为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点曙光,一切都开始变好了,可为什么呢?为什么还是会有在乎的人离开。”
一大段话语似倾诉又不似,或许她就不应该奢求陆羡之能理解她的心情。宁晞眼睛一眨不眨,说到后面更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“从小到大,在我心里,荀濯丞相是如同亲人一般的存在。”
阿翁、娘亲和爹爹死去的时候她有多痛苦,现在也丝毫未减。
一日为师,终身为师,她还有很多很多东西都没有学会,老师却不愿再教了吗?
那双明亮好看的眸子此时被泫然水雾笼罩,仿佛轻轻一触碰,里边就可以涌出眼泪,将他的手掌全然濡湿。
事实也的确如此,仅仅是感受着掌心的湿意,陆旻的心脏生起刀绞般的疼痛,白皙长指不自禁轻抚上她染红的眼尾,企图将泪痕一点点拭去。
他看人待物向来全凭理智,以至于极度漠视情感将悲喜皆置身事外,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,他所有的自持淡然唯独会因她的喜怒哀乐而纷乱。
他想不通是为什么,也不想寻根究底去得到答案。
疏月侧过脸抬袖拂泪,发觉了站立在门口的清俊身影,不知何时来的,也不知听了多久。
她擦干眼泪见礼道:“荀陌公子。”
这道声音打破了满室怆然沉重的静寂。
宁晞闻声渐回拢思绪,眨了眨眼,缓缓转身就看到了广袖飘飘,怀中抱着精致木盒的荀陌。
一眼认出,那木盒,是她四岁生辰时,阿翁亲自与匠人一起为她打造的。
彼时她好奇追问为何要送她一个大木盒,阿翁则慈祥笑着对她说:“梨木清雅,汇日月精华,可用以存智。”
正是开始读书明理的年纪,结合阿翁话意,她想当然地用来存放着荀濯丞相布置的一些重要课业。
此刻对上荀陌沉静似水的面容,直觉告诉她,他对一切也早已知情。
荀陌与陆旻视线交汇不过一瞬,眉目微敛,定了定神径直朝宁晞走来。
“阿晞,世父要我转交给你的。”
宁晞盯着那依然如新带着幽香的木盒愣怔失神许久,才伸出双手接过,放在案上小心翼翼打开,书卷上方,整整齐齐摆放着一封帛书。
缙帛胜雪,上面熟悉的墨色字迹遒美非凡,飘逸如风,又不失松柏傲然之气,亦如那提笔书写之人。
“春三月,气渐暖,虫语莺啼,草木向荣,正值万物复苏时。故,于此间离去,或可换新生,逢故人。余垂垂暮年,行将就木,每每念起往昔诸事,竟也涕泪沾裳似稚子。遥想弱冠之时,正遇山河破碎,风雨飘摇,余空有嗟,尝观漏窗月,独坐至天明,可叹可笑兮。所幸天非薄情,濯得遇明主以明志,因而入仕。濯随武帝退敌军,平叛乱,复失地,戎马倥偬二十哉,得以定江山。自古虽无永固之朝,然大乾气数尚未尽,今经十年窃位,骞北七失,民生凋敝,濯难辞其咎,遂以肉身残躯,谢罪天下,惟愿大乾国祚绵长,与民永康。夫太上之道,生万物而不有,成化像而弗宰。濯赘语至此,诀别之际,浅以一得之见与卿言,为君者,重任在肩,朝中制衡之道,需恩威并施,宽严并济,凡是人才,尽为己用;人世谋福之策,当以民为先,哀民多艰,不居功,不自满,求仁得仁,方成恒久。”
帛书内容不长,娓娓道来。
宁晞眸光缓慢辗转过上边的每一个字,颊侧泪渍也渐干。
看完后久久未语,只小心翼翼将帛书叠好放回木盒,合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