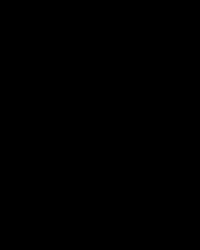笔下文学>用宅斗套路一统江湖 > 第 64 章(第2页)
第 64 章(第2页)
“既然所议之事皆系于我身,”她声音平稳,一字一句,穿透喜帕,“那么,是否也该容我本人,说上几句?”
可陈宣一把就将她拦了下来:“七娘莫怕!一切有为父给你撑腰。”
“是啊,一切有我与汝父,”难得的,袁冀州和陈宣统一了战线,附和起来,“此间自有长辈做主,新妇勿需多言。”家里的女儿已经在人前丢人现眼了,他可不想未来儿媳也在此时搏出个不安于室抛头露面的名头来。
紧接着,两个爹又开始打起嘴仗来。
陈妙之在红色纱幔下,目睹着这一幕,生出一丝荒诞来:明明是自己成亲,可半句都插不上嘴。
故而自古以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,可即将步入婚姻的自己,竟然也无法对自己的命运插上一句话么?
思绪混乱间,她只觉得气息窒闷,眼前这片象征吉庆的红色,仿佛堵住了她的口鼻,令她不能呼吸。昏沉恍惚间,她抬手抓住了那覆于顶上的喜帕边缘,用力向下一扯!
喜帕瞬间落地。
没了遮挡,清冽的空气涌入鼻息,让她混沌的头脑为之一清。
可随之的,惊呼声响起。
满堂宾客错愕地看着她,看着这个不守礼法,居然大庭广众之下,公然摘了帕子露出面容的袁家新娘。
陈宣原本还在和袁冀州对峙,听到呼声,顺着众人目光回头,却见到这一幕,立刻吓得魂飞魄散。
此时也不管袁冀州如何了,只捡起了被陈妙之扔在地上的喜帕,想要重新盖到她头上:“使不得使不得!你忍忍,有什么事儿等回了家再说。”
陈妙之只偏头一躲,就躲过了那块喜帕。
她几步又站回了大堂正中,面对着众人的直视,挺直了背,目光平静地迎了上去。:“既然是我要成亲,那么到底愿不愿意,也该来问问我。”
此言一出,不啻大逆不道。
霎时间众人看她的眼神,都变得意味深长起来:哪有好人家的女儿,大庭广众的,面对一群外男,擅自摘了盖头,还开口说话的?再说婚姻一事,自古以来就没有女儿说话的份。这陈家七娘的言行,简直是悖逆伦常、惊世骇俗!
一直杵着装木头的袁定舟,在此刻也感知到了不寻常,隐隐的,他知道这回是终将彻底失去陈妙之了。他惊慌着上前,想要抓陈妙之的衣袖,又生出了瑟缩,终究把手缩了回去:“七妹妹,你别说了。一切的事,等咱们拜完堂再料理。时宜的事,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”
陈妙之回过头,目光落在他苍白惊惶的脸上,只一瞬便移开:“袁公子,你我的婚约,就此作罢吧。”
接着,她重新回过头,面对着数百的宾客,朗声说道:“诸位高朋在此,皆为见证。我陈氏七娘,不愿嫁与袁氏为妇。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主意,和武庸陈嫁,和桐川袁家,都无关系。”
“轰!”
短暂的寂静后,巨大的哗然如潮水般席卷了整个喜堂。宾客们脸上都是骇然与难以置信。自家揭了盖头已属惊世骇俗,如今竟还当众开口悔婚,这陈家女儿莫不是真的疯了?
“妙儿!住口!”陈宣第一个反应过来,脸色煞白地扑上来要去捂女儿的嘴。
固然他也想撅了袁氏这烂摊子,可女儿自己开口悔婚,和由父亲出面斡旋退婚截然不同。从此她就要背上悖逆狂诞等恶名,莫说是再找户好人家嫁了,就是坐产招婿都没正经人家孩子愿意上门。
袁冀州也气急败坏:“陈七娘!你可知你在说什么?!此乃父母之命,岂是你说不嫁就不嫁的!”如今自家的名声算是全毁了,女儿疯癫异常,儿媳也大逆不道,明天关于袁氏的绯闻怕是就要传扬天下了。
陈妙之一个从容的旋身,就躲过了父亲的手,她继续立于喜堂之中,承受着众人复杂的眼神,依旧淡然:“是我陈七娘离经叛道,此事系我一人所起,也由我一人所担。往后种种,若要追究,只管追究于我一人。”
陈妙之看了陈宣一眼,迟疑了一瞬后,复又变得决绝起来:“我自知违逆纲常,自此之后,我自愿脱离武庸陈氏宗谱。往后武庸陈氏并无我陈七娘。”
此言一出,陈宣的面容,失去了所有血色,变得铁青:“陈妙之你在胡说什么?你是疯了吗?!你不要这个夫家可以,怎可连父母宗族都不要了?这是能随口说的话吗?”
“父亲,我不愿再拖累自家名声了,”陈妙之看向他,努力试图挤出一个笑容,可实在是无法做到,“姐姐妹妹还要议亲嫁人,不能因为我,连累她们。”
“你就听你娘瞎说!”陈宣急火攻心,开始口不择言,“有你姐姐在宫里坐镇,你就是杀人放火,咱家姑娘也好嫁得很!”
这一些上不得台面的话,却是不争事实。众宾客只彼此间看了一眼,露出一个心照不宣的表情:的确如陈宣所说,只要那陈五娘手握盛眷,其他姑娘就不愁一个好婆家。甚至陈宣当局者迷,七娘固然如此不堪,可只要她是淑妃唯一的嫡亲妹妹,舍了这袁家,依旧能找一户不错的人家。
自古以来,人心向背,不外如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