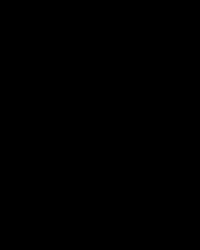笔下文学>青云昭昭(探案) > 第 90 章(第2页)
第 90 章(第2页)
左不过是这几日中择一天。
“嗯,都听你的。”秦艽笑得合不拢嘴,下意识想捏捏她的脸蛋儿,抬起蠢蠢欲动的手才想起这可是在大街上,有碍观瞻,只好按捺着又垂下手,目光缱绻地盯着她看。
两人这十分孩子气的一言为定,看得明秋欣慰一笑,暗自摸了摸眼角的泪水。
她想起十几年前那个仓促的夜晚,那时她与薛赟假作夫妻,逢场作戏,自是连场喜宴都不曾有。待到后来二人心意相通,时机已过,早没机会补全,不免叫彼此都留有遗憾。他们没有喜宴,没有宾客,只有两只大红的喜烛和一盅同甘共饮的合卺酒。
如今女儿三书六聘样样俱全,让新人自行操办虽是有些不合礼数,但只要两人心在一处,旁的都不重要了。
待母女两人采买了一整日,回到院中,明秋便从箱底翻出一直红木妆匣。
打开来,竟是一套熠熠生辉的簪花冠。
九树缠枝牡丹纹的冠上花钿垂珠,两侧步摇呈双凤簪的样式,眉心坠着一点精致小巧的红宝石。昏黄的灯烛下,这枚粲然生辉的彩宝恍若明珠流星,耀眼夺目,映得周遭一切黯然失色。
薛灵玥惊了惊,这样做工上乘的物件在长安都难得一见,更不用说偏壤的幽州了。今日她们看过的花冠,自是没有一顶能与它相比。
明秋的指尖轻抚过步摇上的垂珠,眼中泪光闪烁:“这是当年你阿耶送我的,因我二人没有这个机缘礼成,便留个纪念。我一直小心保存,便是从朔州逃离也不曾丢下。如今我将它交给你,”她颤抖的手抚摸着薛灵玥柔软的鬓发,“让我的女儿,戴着它风风光光的出阁。”
家中的小女郎长大了,他们做父母的不说拖累,却也给不了什么。平阳王蒙冤而死阴差阳错桎梏了他们一生,但灵玥不同,往后天高海阔,她只盼望女儿从心而活。
薛灵玥眼眶一热,随即唇边绽出笑意,忍着泪打趣道:“您说这事巧不巧,我头回与秦艽熟识的时候,便是在个贼窝里假做他娘子。原来您与阿耶当年竟也是这样。”
母女俩的际遇,竟是相同的巧合。
真真因缘际会,天作姻缘。
明秋也笑了,擦掉脸上的泪,揶揄道:“快别往你阿耶脸上贴金了,他就是块木头,你比你娘有眼光,秦郎君体贴明礼,比他强多了。”
话音未落,屋外传来几道重重的咳嗽声。
“听听,还不乐意了。”明秋噗嗤一笑,将花冠放下,朝门外道:“也没几日了,你心疼灵玥便进来与她说说话,别再外头装模作样,摆着一副架子给谁看。”
薛赟臊着脸走进来,身后还跟着垂头不语的薛明霁。
一家人谁也没有先开口,但烛光下,所有的目光都汇聚在那顶耀目的花冠上。
因这一场意外的婚事,他们又将重新聚起,以家人的名义。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庄中的仆役都是昔日裴令仪麾下的老兵,在战场上伤了肢体,或毁了容貌,面目骇人,无处可去,便留在庄中做事。
故而这群人忠心耿耿,更是有一把子力气,听闻薛灵玥与秦艽要成婚,他们一早起来便在庄中里外忙碌,洒水打扫,连水缸中新栽种的睡莲叶儿都擦了一遍,光亮亮,水灵灵的。
新裁的红绸扎满四处,高挂堂中,衬得整座庄园喜气洋洋。
后院的俞老丈是养兽的好手,不出两日,秦艽打回来那六只雁就在他手底下焕发新生,黑豆般的眼睛炯炯有神,昂首仰脖,一见盘中播撒的谷粒,立刻垂头啄食,
时不时在院中抖抖羽毛,张开翎羽,神气十足,比新郎官儿还有派头。
除了大雁,秦艽另置办了几样上等的器物用具,吃食点心,暂时放在院中的供桌上,算作先前纳采的礼数。
待到第二日正午,庄子大门四开,看门的老汉背着手,满脸的褶子都藏着笑意,脸上再无警觉顾虑。他面前,整整六十六担红木箱奁一水儿的扎着红绸,沉甸甸地压在运送的劳夫肩上,远远望去,犹如一条朱漆长龙跨过门槛鱼贯而入。
众人齐力将数十花盆摆件通通移到旁处,把正院腾空,用以摆放。
薛灵玥对他的排场早有准备,先前嘴上虽是说不在意,这会儿看着一院子的聘礼,翘起的嘴角却怎么也压不下去。她大方收下聘礼,依着礼数回以一对雁衔鱼符白玉佩。
谁都想得个知心用情的郎君,除了此刻略显愁眉苦脸的薛家人。
薛赟将明秋拽到角落,忧心忡忡道:“你也真是,昨日灵玥压着不许你买,你怎么能听她的呢!今日秦郎君下得聘礼如此丰厚,两厢这般悬殊,来日咱家灵玥岂不要被他压一头去?”
说着,他从袖中抽出一叠飞钱:“咱家虽比不得长安城里大富大贵的人家,好歹还算有点家底儿,你快再到城中置办去,万万不能短了我女儿!”
明秋没好气地看着那飞钱,“你个瓜脑子,我再给灵玥买套红木家具来又有何用,叫她端着去会州上任吗?还不如直接将这些钱给她留做私房,日后傍身用。”
薛赟默了默:“也成,那你再给灵玥添些。”
“这事还用你说,我早就备好了!”明秋嫌他啰嗦,翻两个白眼,“再匀些出来,会州偏僻贫瘠,去了少不得要置办东西,这些哪儿够!”